劉芷蕙(Mira)擁有豐富的舞台監督 (DSM) 工作經驗,近年經常接觸偶物製作、場景及插畫設計等工作,徘徊在看似講求理性與感性思維的崗位之間,閱讀對她來說有甚麼影響?
閱讀經驗累積個人觀點
早在小學時期,Mira已喜歡看推理小說,中學喜歡看散文,大學修讀的英文專業,使Mira經常接觸很多不同類型的文字,如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劇本、現代文本等,也由那時起開始有看繪本及畫畫的習慣。「當時學過的東西對我現在做劇場是有幫助的,至少可讓我看待事情有自己的觀點。有個人觀點相當重要,絶對有利於與導演、音樂或燈光等設計師溝通,因為當一件事不能用實質的文字形容時,便需要尋找共同語言去討論大家想要的節奏和氣氛。」她補充,舞台監督最基本的工作是控制一個演出的所有技術點,包括燈光、音樂、佈景等,協助導演和設計師達到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層面;作為DSM,看劇本是必須的,因為可以從文字中理解到每個場次的氛圍。「DSM有趣的地方,是沒有正確的Cue point (技術點),要考慮音樂、燈光何時出,Cue point不準,會令戲大打折扣,遲一秒、早一秒都會有分別。因為DSM需要『Go Cue』,這件事本身就很依賴DSM如何理解導演的說話,以及其他演員、設計師對於文本的揣摩,如何呈現這套戲的節奏。」
在繪本中尋找創作元素
在創作方面,繪本對Mira的影響比較大。「繪本是不用很多文字敍述的情況下,只看畫面已經可以講到很多東西,讓人感受當中的藝術氛圍,並有所想像,即使其他語言的繪本也沒關係。」Mira認為,繪本有很多細節令人回味,而且還能看到她最喜歡的媒材——油畫。「從中可以看到色彩的組合,各公仔的比例,這些元素其實已經可以呈現到這個畫面想說的話。每本繪本都有不同的插畫與文字風格,與作者想表達的主題十分有關。正如不同演出有不同風格,導演給予我的指示,對於我去思考演出所用的偶物類型、形狀、大小比例、顏色分配等,都會有影響。有時候我會一邊做道具一邊想像,偶物該如何『亮相』才能切合到文本?到底是忽然出現、慢慢出現,還是一直已經存在?當然,演員如何操偶,亦牽涉我如何製偶,不同操偶的方法都會影響整套戲的風格。」去年的《當鴨子遇見死神》校園巡演版,便是由Mira負責做道具。「當時與導演討論,希望這個巡演的版本可以與原版繪本不一樣,因為與同學的距離十分近,不想鴨仔有種被操控的感覺,我便以一個舊公仔的概念製作主角鴨子,像是演員在玩這個舊公仔,而它已經安靜地在家中陪伴你很久,現在要向你訴說故事。」對Mira而言,演員和導演已經在文本的傳譯上賦予了很多,在視覺上應如何令整件事看起來更加連貫,賦予更多意義?如何做到小朋友或者導演想要的效果?「這些意義不單是文字可以敍述,有圖像或視覺上的focus(焦點),是我希望在創作上可以做到的。」
道具與象徵
「喜歡製作道具,是因為對我來說,道具不只是一件道具。」因此,Mira喜歡在繪本中尋找「象徵」。「在陳志勇的《夏天的規則》中,每一頁都有一隻烏鴉出現,像是陪伴着這兩兄弟成長,當夏天過去了,弟弟有所成長,烏鴉也消失了,這些象徵物對於我去看演出,或構思整個作品的脈絡都有幫助;當然,很多時候導演對演出都有自身的看法,未必由我去思考故事的flow (流動),但我都喜歡去找象徵的顏色和形狀,去反映文本某些東西。我做作品,都會挑選最重要的部份出來,希望可以在演出裡提示,這些象徵的意義對我來說也很重要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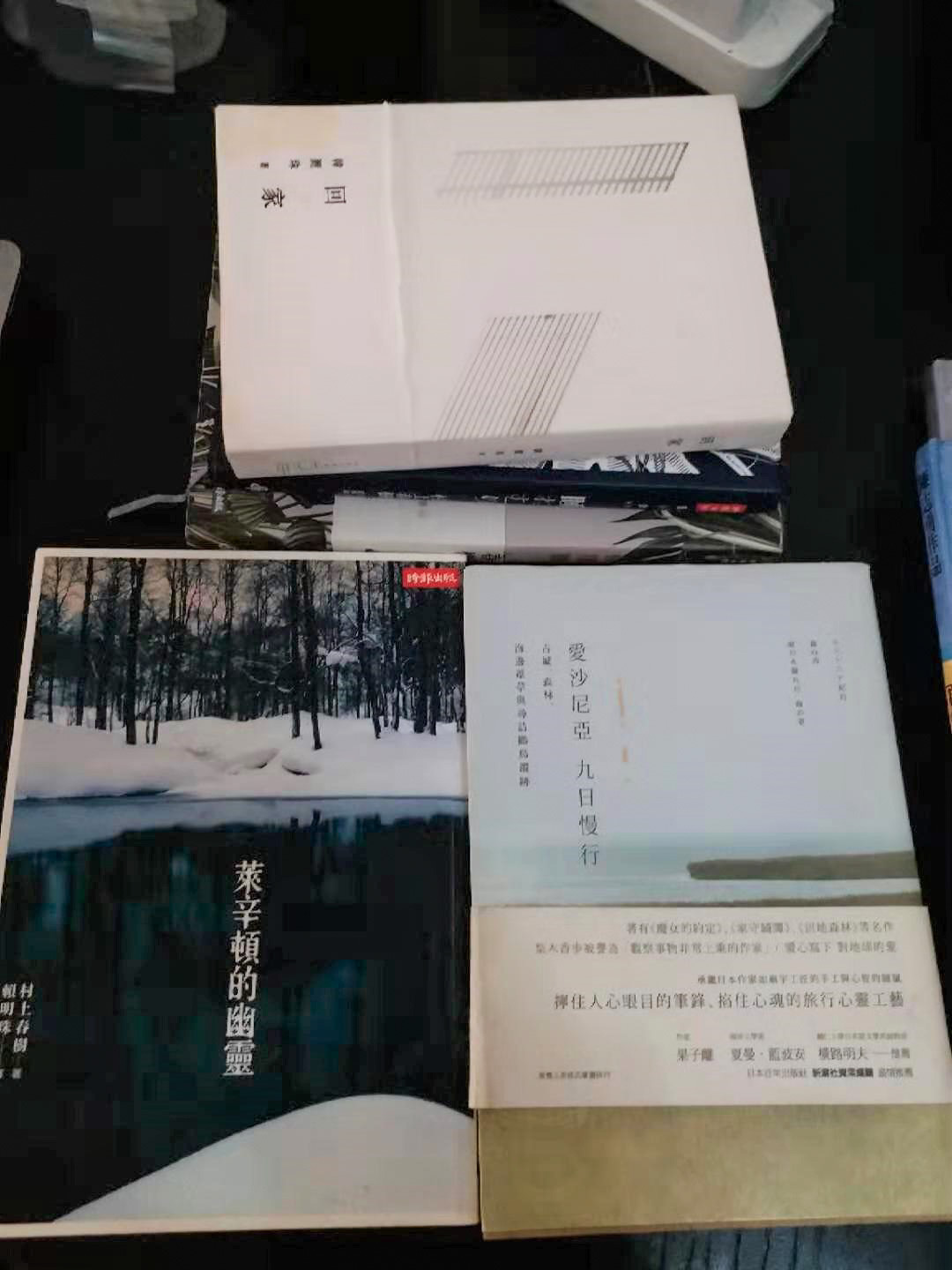
除了繪本,Mira平常喜歡看一些與工作無關的書,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、三浦紫苑,香港作家韓麗珠的散文。「看散文好似與創作無關,但看完文字後,對情景的某些想像會紮根在腦海裡,慢慢累積。這些氛圍對於我在畫畫、做道具或場景都有視覺設計的投射。如韓麗珠的《回家》,內容描繪主角在回家時在路上看到的風景,書的文字風格並不寫實,但從文字中可以好清楚看到香港這個城市的輪廓,看着又會覺得文字好像在描述另一個世界。將對城市的刻劃及表象變成一個象徵的這種手法,是我喜歡的風格。」
「閱讀經驗使我更為開放,對於文字,對於演出,基本上都是持開放態度。」Mira這樣回應著:「很多時候,做劇場都需要用很多東西去包裝一件事、一個主題,但也可以想想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去講故事呢?新起一個文本,如果需要做道具或偶物,很快可以與導演討論要甚麼風格,因應所需風格做適合主題的形象出來,這是我一直努力做的事。」

